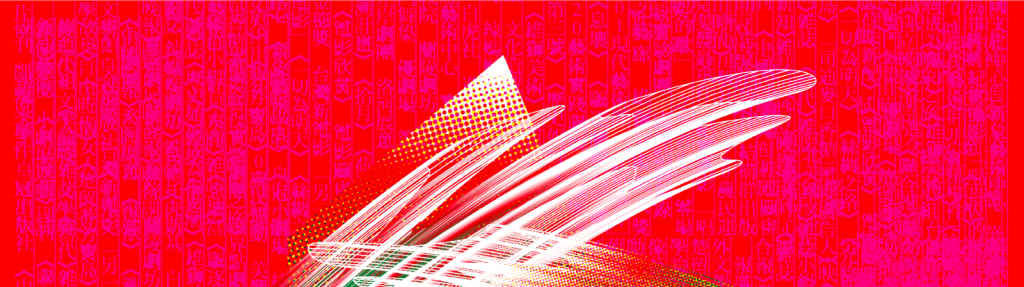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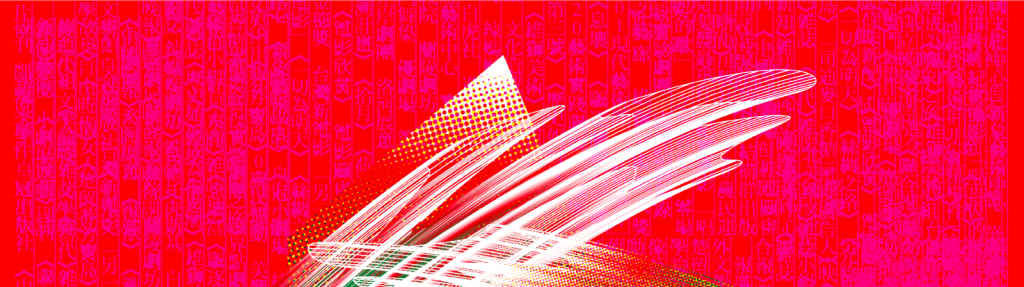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精神在於以社會和歷史的環境變遷,調查研究臺灣總體當代藝術發展的脈絡及動力,並特別聚焦在80年代這一跨領域濫觴的時期,以此探究現當代交接之際的文化力生成及其影響。此外,本研究的規劃並不僅僅限於學術上的推演,而是包含田野探訪、交流活動與展演準備等多元連結作為指標,並期望開展出研究經驗的積累空間,讓研究所得的材料與論述能夠連結上相關公共的數位資料庫建置,藉此通過在地的有機論述發展與深入在地藝術現象,而致力於在「跨領域」脈絡下,探索臺灣特色之「文化力」,並與世界連結對話。
「跨領域」一詞的使用幾乎和「跨國」或「國際化」同時出現在1990年的臺灣,但這時引發的「跨領域」首先明顯的是文化關聯性的延展,以及關於領域間對話合作的「概念」,屬於超前的召喚,而不是對當下經驗或實驗的指認;甚至更準確地說,是來自某些地區的先驅性發展經驗, 80年代中期後國際上重要新媒體藝術機構相繼成立,如IRCAM(1977)、V2(1981)、MIT Media Lab(1985)、ZKM(1989)、ICC(1990)等。但如果我們關注實際經驗的發生時刻,會發現從70年代末以至於整個80年代,並延伸至90年代初,都可以找到「跨領域」經驗的足跡;90年代「跨領域」的指稱仍是為了追隨時代與國際的腳步(當時主要是不同藝術領域間的合作),只是這項概念式「跨領域」的打開,特別是不同領域間的連結,在一種水土不服的狀態下,不由得在另一層面迫使我們需嚴肅面對「本土」經驗。
儘管通過「西方」進步概念促生就地的拼裝、改造與躍進,和60年代通過文學、電影、戲劇的翻譯,促發《劇場雜誌》等各種實踐與實驗的條件,確實有其相近的連繫,一種不斷通過「殖性」而引發的張力和歷史脈衝,才會出現倪再沁於1991年三至四月,對於臺灣美術發展的根本性批判;但同時間,我們也會發現他當時的研究框架中並沒有含括《劇場雜誌》,以及對於70年代末蔣勳在《雄獅美術》「跨領域」規劃的忽略,於是實驗性、跨領域脈絡與殖性的關係也就錯過了倪再沁的犀利考察。那麼,關鍵就必須著眼在理解實驗性的經驗是如何因環境而自發引動,而不是通過專業性的教導、學習和想像誘導驅動?雖然這兩者在置身現實經驗或通過論述取徑都不容易明確區分,甚至我們必須理解到「自發引動」與「誘導驅動」在臺灣是兩種不可能個別發生的狀態,但同時之間又存在本質性差異,所以必須經由兩者關係上的差異性來考察;其一在社會狀態的要求下自發引動的構思和實踐,外來訊息與概念在此僅作為參照,另一在解放的企求下擴大外來訊息與概念的想像,期待在這誘導下能推動社會與文化的改變。
1970年代的外交困境,使得臺灣對於「主體性」(當時主要以民族精神或民族自尊來指稱)的迫切要求促生了臺灣文化工作者對於掌握在地現實的重要性,於是,一方面衍生而出的民俗與民藝的調查蔚為當時藝術家與文化工作者大量投注的風潮;另一方面,從70年代初開始並於1977-1978年達到白熾化而驟然結束的鄉土文學論戰,無論是論戰中的哪一方都一起投入創造了臺灣的現實內容,也在70年代末對於美術圈造成極大的鼓舞。所以1976 年王淳義在七月號的《雄獅美術》以〈談文化造型工作〉發聲提出「文化造型」,他對西方藝術形式與藝術教育提出了尖銳的批判,儼然觸及我們今天以「後殖民」一詞所談及的許多面向,並以民俗研究和調查為基礎來思考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反抗姿態。然而蔣勳對於造型工作進行確實的檢討,帶入社會文化想像,乃至於提出「全面文化造型」。70年代主要以「民間」作為現實,與高等教育所樹立的外來及傳統價值相對抗,嘗試基於在地經驗、揉和西方知識的未來想像。
因此,我們理解到跨領域在臺灣經驗中並不是完整分工後不同領域間的連結與合作,相反地,常見的是「跨領域」的驅力往往出自對專業性(完整分工)的追求。為了能即時接收新的專業訊息、精進專業工作、創造專業氛圍與環境,所以熱切地與人交流、搜羅訊息,甚至致力於轉譯和書寫,交流、精進、氛圍、環境、翻譯、書寫正是臺灣「跨領域」的徵兆與型態,這種「跨領域」型態會朝向形式的模仿與複製,但同時可能朝向促成真實經驗的發生,前者指向形式與文化權力的連結、朝向未來,但卻是一種被殖民的他律狀態(即世界接軌[cosmitte mundo]),而後者則指向實驗與認同的重疊、時間性的裂縫,是追求獨立性的自律狀態。前者多數追隨西方現代形式而獲得大多數即時報導的版面,而後者則深入到對自身感受與環境特質的判定,以此作為經驗發展的依據,但卻難得被相關媒體報導(除了轉向民族主義與在地的70年代)、分析和認識;同時因為這種自律性的經驗實驗和創造需要相應的語言來再現,無法直接引述歐美形式分類與概念(雖然勉強為之還是大有人在)來清楚說明,往往產生「寧靜災難式」的延遲。林惺嶽見證70年代的「鄉土運動」有感而說道:「任何一種文化運動,要開拓出真正的新境界,務必具備自動自發的內涵」,因此,即使半世紀前的「鄉土」這一帶有「抽象性」含量的指稱有其時代特殊性,但還是需要擱置「鄉土」這個容易在今天引起混淆的詞,而更嚴肅地追索、對待所謂「就地」發生的狀態和事件:就地創生(terra genesis)。「就地」不再強調「故鄉」或「在地」的指稱,也絕不是某種本質的確認和特性的界定,而是實驗與發生的「繁生」時刻,「養土」,正如「息壤」一詞所言。
這樣的就地創生(terra genesis)在70年代的十年「鄉土運動」後,同時發生在文學、電影、劇場、藝術、文化採集與人文科學等場域中,更確切地說,發生在這些場域的劇烈交流中,如「雄獅美術改版」、「文化造型」、「鄉土文學論戰」、「息壤」、「臺灣新電影」、「實驗劇場運動」、「戰爭機器」等等,生成一個匯聚能人、活潑強力的80年代。從60年代到80年代中的變化來看,60年代是進行翻譯實驗的時期,以抽象拒絕壓抑,70年代在危機中開啟文化田野、用追尋過往拼圖在地,而得以跨越「鄉土」與「西潮」二元對立的80年代,有了前面十幾年的經驗、思考與積澱,在充滿懷疑與渴望中迸發出各種事件性的「就地創生」,從連結中追尋未來,其中最為特別的就是「就地創生」與「跨領域」如此貼切地重合。「就地創生」中的「就」凸顯出本土衝動下「當下立即」的意味,這意味主要為了同「鄉土」中的根源性區分開來,而「就地」則是在關懷本土衝動下面對確切地點(in situ)著力其上、發出行動,簡言之,用「就地創生」來取代「鄉土」甚至「本土」,主要為了迴避掉「根源性」並需要強調以「類聚」(gathering)作為行動的「事件性」,以確切強調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臺灣特殊性。
因此,本研究計畫案旨在審視臺灣當下「跨領域」的現象時,不以「國際/在地」、「西方/東方」或「他律/自律」來理解這兩種狀態,而是回顧臺灣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歷史現場及現實,並認知到「差異」就位處於慾望中自律性與他律性所區分出的實踐程序上。